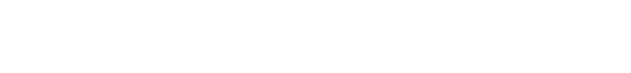语学院自2013年开办“海外名家系列讲座”以来,已举办了二十六讲。近日,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张英进教授应该前来为“海外名家系列讲座”作演讲。2014年10月22日下午,他来松江校区为我院师生作了“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跨学科的思考”学术报告。讲座由查明建教授主持。讲座吸引力了全校众多研究生前来参加,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讲座开始前,查明建教授首先介绍了张教授的研究方向及著作情况,而后强调此次讲座对于了解比较文学、尤其对了解国际比较文学的前沿动态有重要作用。
随后的讲座中,张教授开篇也讲到这一问题。他认为,经过近30年的努力,国内比较文学学科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一门“显学”,更需要与国际接轨,寻求国际性对话,这也是此次讲座的背景原因。
讲座围绕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这一主题展开,主要是系统性地介绍了自八九十年代至今美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动态。张教授首先介绍90年代该学科的发展情况,他以93年“伯恩海默(Bernheimer)”报告为例,指出这份报告以“多元文化”为标题,强调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直接挑战六七十年代以欧美为中心的精英文化传统。历史、文化、政治、地点(location)、性别、性取向、阶级、种族等等这些因素被考虑到阅读之中,文学的语境扩展到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及性别等领域,使得研究文学的方法与根据作者、民族、时代及文类(genres)等旧模式的文学研究已经迥然不同。
张教授还提到美国学界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问题。他以克里格(Murray Krieger)的观点为例,阐述美国文学研究在50年代进入了“批评的时代”,至60年代又被“理论的年代”所取代,这其中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本身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克里格的观点在九十年代的美国文学研究界属于少数派的观点,但他代表了一些刚刚是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一代理论家对文学研究学科转型的焦虑,所以很能揭示美国人文学科机构的变迁。之后,张教授以杰拉德·格拉夫(Graff)的观点阐释当时美国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格拉夫认为用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来抵抗批评理论是历史上时不时发生的现象,因此对批评理论取代作品的研究的焦虑是不必要的。格拉夫担心的问题不是1980-年代后“理论的爆炸”会摧毁传统的“人文神话”,而是学科史中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即“先锋理论”常常被文学研究机构所正式接纳,最终“屈居一隅”,失去其早年的先锋性。
在西方与中国的学术争论方面,张教授以周蕾和张隆溪的学术争论为例进行阐释。周蕾首先承认西方理论的霸权地位,然后投身西方理论以求“发言”的权力。而张隆溪对周蕾完全认同西方理论的立场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她有意混淆了理论的虚构性和现实的存在性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强调“中国现实”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主张文学研究者以自己的经验来感受,比较中西文本,从而达到真正的跨文化的理论高度。
之后,张教授还以阿玛德(Ahmad)对杰姆逊(Jameson)的批评为例提到了“理论市场”。阿玛德认为,理论渐渐成为少数批评家进行相互对话的主要渠道,这类对话是一种特别的知识生产过程,它提高了批评家的地位和身价;他进一步揭示了文学激进主义与全球时代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理论本身成为思想的市场,成为可以使用的商品,保证消费者的自由选择”。“理论市场”的比喻仍可以解释文学研究机构化过程的某些现象,因为某种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的兴起于衰退可以理解成文学机构对思想市场进行供求关系所进行的调节的结果。
张教授对此作出评论,认为由于市场的机制,“消费者”的选择并不像阿玛德所说是完全“自由”的,不同的“商品”和立场的选择也必定造成不同的结果。像阿玛德那样保持距离地批判文学理论的“商品化”而不愿完全投身理论的市场,其结果是被市场边缘化、进而被逐步淘汰。而相反,象周蕾那样一心投身理论的市场,从西方的理论内部批评西方理论的盲点或薄弱之处,其结果是被市场中心化,纳入美国学科机构的主流话语,反讽地成为西方理论界中“非西方”的发言人。作为思想的市场,西方理论不断地需要建设性的批评来完善自身,并以此标明自身的合法性(过程“民主”)权威性(理论“精英”)。
在介绍了90年代的学科发展情况之后,张教授又着重介绍了2003年的“苏源熙(Saussy)”报告及相应回应问题。2003年的报告则更重视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回顾和对比较文学“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之利弊的思考。早年的回答认为比较文学史包括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以及超越国别的共同的文学发展模式,但这些回答被认为是比较的方法,而且,这些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其他学科(如英国文学、艺术史)同样可以使用,因此不能成为比较文学独一无二的学科定义。因此引发了该学科的学科危机,其中在2003年的报告中,嘎亚特力·斯皮瓦克宣布“学科的死亡”。之后罗蒂(Rorty)对此的回应是,“危机”乃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所谓的“危机”将学科中貌似边缘的东西推入中心,将貌似中心的东西推出黑暗的边缘:学科就是这样重写自己的历史,不断刷新自身的形象,所以可以说只有学科的种种历史(复数,因为重写 histories),而没有学科的固定本质。由此还引出“星球意识”的概念。近年来斯皮瓦克同一些学者倡导文化批评从“全球化”到“星球意识”(planetarity)的思维转向。斯皮瓦克建议用“星球”(planet)取代“全球(globe ),因为星球属于另一个系统,代表了”他者性“(alterity),甚至超越了人的视角。
张教授对此的看法是,星球意识的理论无疑将有助于重新阐释文学与自然、生态、甚至宇宙观的关系,这对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十分有利。但是,星球意识理论具有极其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乌托邦式的思维。相比之下,“世界文学”具有实际教学意义。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也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承认的政治”及“承认的技术”,如果不被欧美主流机制(出版、媒体、大学)“发现”,这些非中心的文学就默默无闻、形同无存;第二个问题是阅读的方法,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欧美文学教授南面坚持西方中心的阅读,他们的阅读自然有别于本土文化语境的阅读;第三个问题是单向的翻译,没有英文的翻译,无论其作品如何杰出,都很难被西方权威承认。
此外,张教授还总结到,2003年的报告提倡“文学性”(literariness)作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比较文学不仅要“比较地”研究国家民族文学(这是传统的观念),更要“文学地”阅读自己研究的对象(如今已不仅仅是文学,而包括其他的话语实践)。
在介绍了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之外,张教授还结合他自身所经历的四所大学,讲述美国高校中比较文学建制及其教学观察的一些感悟。首先是对博士语言和理论的要求上,传统博士学位要求研究三种语言的文学,如今要求两种语言的文学加上一个相关的“领域”(field),这一领域多数是邻近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艺术史、电影研究),但偶尔也可以是更遥远的学科(如建筑、经济、法律、美术创作、生物学、计算机等)。其次张教授讲述了他所经历的依阿华(Lowa)大学、斯坦福(Stanford)大学、印第安纳(Indiana)大学及他目前任教的圣地亚哥(SanDiego)加州大学这几所大学的学科特色,以其亲身经历为同学阐述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几所大学对该学科的建设情况。
最后,张教授对比较文学目前的发展状况作出了总结,并从学科体制的建构与调整、文学理论与文本研究的互动、研究生培养的灵活性和前瞻性三个方面对比了中美两国该学科发展的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和主张。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举手向张教授请教问题,围绕视觉文化、新媒体、学科危机、文学改编与重新创作、“边缘”概念及风景园林等诸多方面提出疑问,张教授耐心地一一给予解答。张英进教授学术视野开阔,在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电影研究方面都卓有建树,著述丰厚。他的讲座不仅帮助同学们了解了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动态和前沿问题,也扩大了同学们的文学研究的视野,感到很有收获。
威尼斯7026官网